


数字时代文艺评论的媒介形态发生了变化,从相对专业化、单向度的评论方式转向互动性、社交化的互联网模式,不仅出现了参与式评论、视频化评论、情绪化评论、粉丝型评论等新形态,而且带来粉丝经济、网络舆情等多重社会效应。本文一方面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分析数字时代文艺评论的类型,另一方面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探究数字时代文艺评论所存在的问题。在数字时代,应该充分发挥数字媒介的主体赋权功能,形成良性的、社会参与的公共媒介空间。

评论是一种总结,还是一种评价?对于不同受众,评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文艺评论的意义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传播及人类思想的传承。评论的“评”与“论”两者虽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并非全然互为附属,而是各有侧重。“因评而论”需尽可能的客观,但客观与否和评论者本身能否透彻理解作品息息相关;“因论而评”则需多些主观,论述不仅让读者了解有关这部作品的前因后果,也带来文艺作品的“附带第二生命”。艺术形式千变万化,但一切皆有结构可循,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评论模式和艺术创作模式亦无两样,文艺评论本质也是一种文化艺术,它有着和文化艺术类似的特点,那就是同样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接受其独特性的见解才是判断文艺评论价值的基础。

新文艺评论是适应新一轮信息革命而产生的范畴,在事态上由新媒体技术的突破引领,由“未来已来”的趋势定义;在意态上察觉人工智能的崛起,既意识到人机竞争的挑战,又致力于发挥人机协作的优势;在情态上不仅充当文艺幻想的解梦师,而且以警醒的态度扮演“奇点”敲钟人的角色。其要旨为关注新变,促进协变,警惕异变。

2021年4月12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出席会议并作主旨讲话。

红色文艺经典的修辞美学是红色文艺经典在艺术媒介技巧、艺术形式风格、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情感思想等修辞方式上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如典型示范、转型再生、破旧立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应当将红色文艺经典纳入中国自己的文艺经典传统链条、并且参照世界文艺经典去衡量,使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成就精华的一部分。它既留下宝贵的修辞美学经验,也同时铭刻下一系列沉重的教训。今天的主题文艺创作要想成为新的文艺经典乃至文艺高峰,需要鼓励长远眼光的创作态度和个性化创造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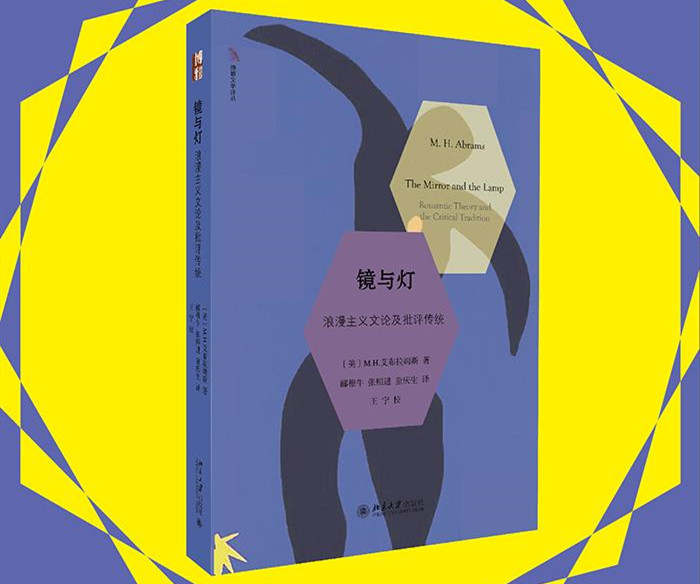
京剧《文明太后》表现北魏冯氏太后的统治,将冯太后塑造得高大伟岸,全力贬抑她的对立面献文帝;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重塑了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形象,按“革命烈士”的理想将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完全扁平化了。湘剧《云阳壮歌》表现红军家属玉姑在等待丈夫胜利回来的15年里一直与救助了她及女儿的男人一起生活,饱受村民误解与嘲讽,该剧所强调的是她始终为丈夫守住了贞洁。三者都是基于主观理念改造历史与人生,导致作品显得虚假的例子。文艺必须兼顾与平衡作品与所表现对象的关系,才能真实可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活各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消费为主导、以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审美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由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二是还原革命历史中的生命个体;三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融入地域文化风情。在开放多元的大众文化语境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叙事视角、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段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突破,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引人深思。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彰显人文关怀时,不能迷失历史理性;在注重平民色彩时,不能消解英雄品质;在追求历史深度时,不能放弃时代高度。

“红色文艺经典”是历史的,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有其定位,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中不断建构;同时,它也是现实的,以其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回到人民性立场,高扬人民性的文艺观,在不断阐释和价值积累中迈向当代文艺经典化。它以文学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创造的丰功伟业和做出的巨大牺牲,是书写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壮举的载体,是讴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挺直了脊梁的情感历练和精神记忆。对“红色文艺经典”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和阐释有四个维度,即历史的、美学的、人民的和艺术的。

本文从红色革命文化对戏曲艺术的作用与影响出发,分析红色革命题材对戏曲文化传统的渗透与改变,由此呈现戏曲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剧种艺术本体、创作主题和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诸多变化,透视革命题材带来的文体叙事的结构变化和戏曲艺术体系的现代拓展。

本文对于红色经典的概念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对红色经典戏剧的发展路径、艺术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指出以“红色”的特有内涵,指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和新事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出现,而“红色经典”一词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以红色历史、革命先驱、英模人物为表现对象的戏剧出现在舞台上。红色经典应具有正确的导向性、艺术的真实性、人物的典型性,应言近旨远、拥有最广大的受众,具有不断被诠释的丰富艺术内涵、完美的艺术呈现和持久的艺术魅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红色文艺经典凝结着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生动创造,记录着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力量,彰显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红色文艺经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有机结合,开掘深刻而又丰富的思想内涵,兼容并蓄、返本开新。新征程呼唤新经典,应坚定文化自信,把握艺术规律,传承革命精神,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红色文艺经典,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自媒体文艺是新媒体文艺阵营中最有活力、最具个性、最接地气、最受欢迎的新型文艺,在2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中,历经三个代次的衍变推进,已经由博客、微博等叠加转向当下最为火热的短视频模式,并迅速构建营造了当下全民参与、全民创作、全民消费的网络文艺快餐时代,其生产速度之快、传播覆盖之广、积聚受众之多、社会影响之大远超以往文艺类型。新的文艺模式需要新的评论手段,面对自媒体文艺评论的短板,如何加强自媒体文艺评论,强化对自媒体文艺的引领,切实营造良好的自媒体文艺生态业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互联网彻底颠覆了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使得文艺创作和评论出现新理念新景象。新文艺评论不仅仅是因传播方式的改变而生成的网络文艺评论,而是在思维方式、价值体现、情感态度、表达手段上运用互联网思维的一种新的文艺评论样式。它具有创作与接受者参与互动、灵活多样的表达、快捷有效的传播等特征。新文艺评论需要对网络作品加以科学理性分析和有效引导,以充分发挥专业性权威性评论的示范带动作用。

生理年龄的代际之差,也会演化成文化和审美的差异。而经过新技术革命的剧烈变革,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是在计算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着特殊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追求,甚至有独特的网络语汇。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新生代成为新文艺形式的创造主体,他们是新生代艺术的创造者和在场者,但在文艺批评领域,新生代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缺席者。然而,经典批评家们在新的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中并不在场,这就构成了批评者与欣赏者的思想隔膜。代际之差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对话,彼此沟通,靠拢而不并拢,交融而不消融,保持艺术形态和审美追求的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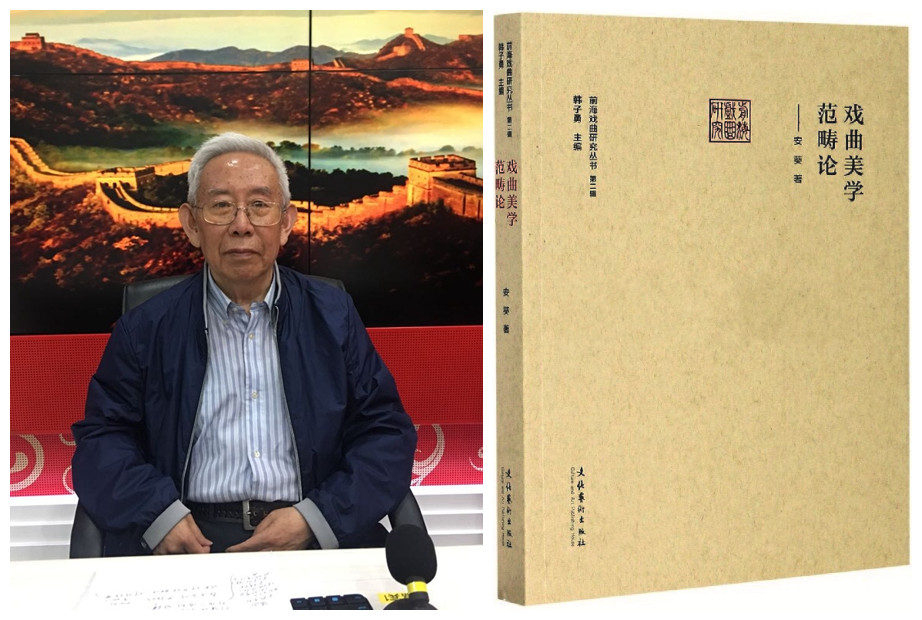
安葵先生新著《戏曲美学范畴论》,以“剧诗说”为建构设想,以形而上的理性思辨和形而下的戏曲理论及丰富的舞台实践为支撑,以“形神论”核心范畴为主轴,通过“虚实论”“内外论”“功法论”“流派论”“雅俗论”“悲喜论”“新陈论”“教化论”“美丑论”系列范畴的辩证发展,从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文本与呈现、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视角,完成了理论体系的范畴架构,呈现出鲜明的创造性、体系性、实践性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020年的中国美术,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主体互动,以此呈现其自觉性。这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与主题性创作有关,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体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关。本文从“主题、主体与整体性”切入,讨论艺术抗疫中的主体多元,以及传统与当代文化中的主体建构,再及公共空间中的大众审美问题。在2020年复杂的中国美术现象中,本文力图抓住典型案例,针对热点问题展开分析,既反映上半年艺术抗疫的整体情况,又通过下半年大量出现的双年展现象,看到文化主体性在创作中的活跃程度,关注在脱贫攻坚决胜之年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性作用,最后提出当代美术学学科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让中国电影业一度停滞不前。在电影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2020年对整个电影行业的冲击、影响及改变可谓巨大且深远。令人欣慰的是,整体疫情的有效控制,防范于未然的观影措施,以及一直砥砺前行的中国电影人,让中国电影业以最快的速度复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在这样的电影发展关键时刻,电影理论批评在电影强国建设中应发挥智库智囊作用,迎接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的黄金时代。此外,面对新的语境,中国电影需要在“共同体美学”的理论框架下形成整体利益观、共同利益观以及平衡利益观,有效应对疫情给电影产业带来的危机和挑战,推动中国电影健康、可持续地繁荣发展。

2020年的中国戏剧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创作演出被迫中断。疫情稍有缓解后,各地戏剧院团就展开了自救,演出陆续恢复,并创作了京剧、昆曲《眷江城》,话剧《热干面之味》等优秀作品。在各地大量出现的脱贫攻坚主题新剧目中,彩调剧《新刘三姐》和客家山歌剧《白鹭村》是值得关注的佳作。江苏、陕西、广东三省相继举办了艺术节,北京和上海的小剧场戏曲节也如约而至。文艺评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次推出的“张庚戏曲学术提名”和《戏剧与影视评论》等报刊发表的系列评论文章,都是对呼唤专业、权威的戏剧评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