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产出的文艺理论“硕果”
——读王一川《心性现实主义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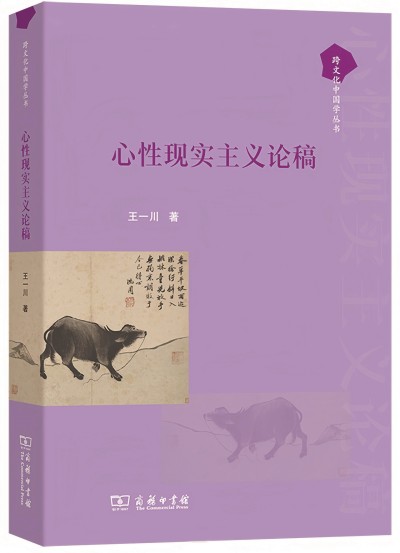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成果。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目前的学者研究更多是对两者“求同”式研究,包括对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如何契合的研究。但两种异质思想文化形态之间是如何结合并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还是一个待展开、待研究的大课题。
文艺理论家王一川先生近著《心性现实主义论稿》就是“第二个结合”指导下,在文艺理论领域产出的沉甸甸的“硕果”。
王一川是一个善于创造新概念的学者,“心性现实主义”是其中一个标志性“发明”。这个概念是否站得住,没有读这本书之前,会有不少人打问号。读完这本书后,问号会被拉直成为感叹号——“心性现实主义”的提出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观念,现实主义创作是我们党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主张,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主要的文艺形态。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出现了“启蒙式”现实主义、“建设式”现实主义、“伤痕式”现实主义、“新写实”式现实主义,这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下文艺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形态。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理论自觉,我们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新时代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表现、新的特征和新的样貌,需要我们的理论家及时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心性现实主义”无疑是其中极具学术价值的探索。
心性现实主义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抓住中华文化的本质特性是探寻“结合”奥秘的前提,从哲学层面入手才能确保理论的彻底。王一川很好地梳理了现代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梁漱溟、张岱年、牟宗三、徐复观、李泽厚、钱穆、许倬云、庞朴和张世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并找到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认知的相通点——偏重于主体心性智慧或心性论的传统。这与注重外向的自然客体或对象的西方文化传统有显著差异。于是乎,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心性”二字由此凸显出来。
新理论确立的关键在于核心观点的提出。王一川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机理命名为“万物通心”,也就是物质决定精神与注重主体心性作用、集体实践方式认识改变世界与重视个体德行修养的辩证统一,并论述了“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原则和实施途径。特别是其中实施途径提出的七个规律(天地生文律、阴阳交替律、刚柔相济律、以善润真律、化悲为喜率、褒贬皆有律、乐以忘忧律),直接关联文艺创作与审美的一般方法,使得悬空的理论得以落地。
现实主义一直以来是多义的理论热词,无论是机械式图解政策和概念的公式主义还是庸俗社会学倾向,或是形形色色各类现实主义分支,或窄化了理论内涵,不利于打开创作空间;或泛化内在规定性,不便于在创作中精准把握。心性现实主义的提出,使得当代现实主义创作有了比较明晰的方向。正如王一川书中所言,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艺总是把客观性置放在关键位置不同,心性现实主义文艺强调需要面对主体心性浸润了的客观现实,也就是始终与主体心性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客观现实”。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借用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的现实观,阐发了现实与文艺中的现实的关系,区分出心感现实、心明现实和心创现实三个层次,为现实主义创作打开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可以说,心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拓展,无疑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遵循两个基本路径。一方面是观念层面的理论衍化和生长,另一方面是实践层面的理论提炼和升华,两个方面统合互济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王一川提出心性现实主义,不仅是文献研究、抽象思辨、逻辑推演、考据论证的结果,同时是立足当代文艺实践,对文艺创作长期观察研究的结果。王一川自2012年起担任《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总论的首席专家。《报告》每年一本,他连续10余年对中国艺术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对文艺实践的情况非常熟悉,基于文艺实践的理论思考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王一川作为活跃的文艺评论家经常参加各类文艺作品的学术研讨,发表评论文章。这些无疑都为他提出心性现实主义奠定了实践基础。
王一川选取了小说、电影、电视剧、网络剧、舞剧、话剧中的代表作品,以心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开展批评。著作中以小说、电视剧《人世间》作为心性现实主义成熟之作着重进行了分析。在再现现实的目的上,《人世间》不单独追求现实再现的纯客观性或真实性,而是以个体心性修为去浸润真实,以仁润真,这既为作品确立了向上向善的基调,同时又敞开了丰富的人物塑造形态,避免了脸谱化、公式化。在再现现实的路径上,以中国传统文艺传神写照的方式塑造典型,各有其“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在再现现实的根源上,地缘化育和时势造人,用中国的语境和场域反映现实主义的一般性要求。在再现现实的态度上,有褒有贬,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反映复杂的心性状态。在再现现实的美学形式上,流洄并作,有历史感和时代性,呈现史诗韵味。可以说,这些文本细读方法检验了心性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论在描述、阐释和评价的应用上得以落地。
王一川还在修辞、叙述体、主体间性构型、地缘心性形象、现代君子人格、大变局下社会心态、个体心象等方面对文艺作品进行学理分析,并把它们都归类于心性现实主义,使得心性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化、系统化。
应该说,一个新鲜理论从提出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这其中一定需要经历过各种批评才能不断完善。尽管笔者在阅读中感到,心性现实主义的许多核心论述还稍显粗粝,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还可以引用国外研究成果,一些当代作品选取可以更有代表性……但作为提出这一论述的第一本专著,无疑它的学术使命已经完成。期待文艺理论评论界可以展开有益的学术争鸣,期待王一川先生及他的认同者、追随者甚至是质疑者、批评者能够把这个学术课题继续下去,共同推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得以诞生并绽放光彩。
(作者:徐粤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